2月28日~3月2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二、三、四讲分别邀请日本青山学院大学佛教学陈继东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陈永革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龚隽教授,围绕“晚清民国佛教”这一主题在新斋154举办了三场专题讲座。

2月28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二讲举办,由日本青山学院大学佛教学陈继东教授作题为“回归释迦:近代中日探寻佛教原典的开端”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陈金华教授支持。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王颂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范文丽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杨剑宵出席本次讲座。
陈继东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佛教被西方的重新发现破题,对西方学界在佛教研究领域开创的印度化、梵文化、文本化和人间化的路径方法以及马克斯·穆勒比较宗教学方法在印度学研究领域的兴起等背景作了简要介绍,对现存于牛津大学、与近代中日佛教研究方法与路径转向关系密切的一封书信进行了解读。该信是对近现代日本佛教研究影响甚巨的著名学僧南条文雄于1879年写给当时正在中国“弘法”的日本僧人小栗栖的书信,南条文雄在信中表达了对小栗栖布教的支持与期待,在与朋友分享自己伦敦留学的经历之外,还提到了他在牛津大学的导师马克斯·穆勒及其对自己的影响,并表示出要在中国探寻梵语原典的愿望。此外,南条文雄还在信中对当时日本佛教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陈继东教授认为,这封信预示了此后在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对理解近代日本佛教研究史的意义重大。与此类似,清末著名居士许息庵致杨仁山的一份书信,也同样预示了中国佛教研究界在历史变革中的方法与路径自觉与改革的决心。在这封信中,许息庵表达了自己重新编纂大藏经的意愿,并且明确提出要增入新搜集的印度佛教梵典,以回应来自儒家、绵延至清末依然势头强劲的攻击。同时,许息庵还从护法的立场,表达了对西方佛学研究的忧虑。
陈继东认为,这两封书信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回归释迦的潮流,但共同的选择背后却有不同的诉求,要言之是与中日两国佛教所面临的问题有关。讲座的最后,陈继东教授以一段在牛津访学时的“论辩”经历作为结尾:佛教史研究,究竟是要重点关注“释迦想了什么”,还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信众们实实在在“相信了什么”?这是一个能够不断启发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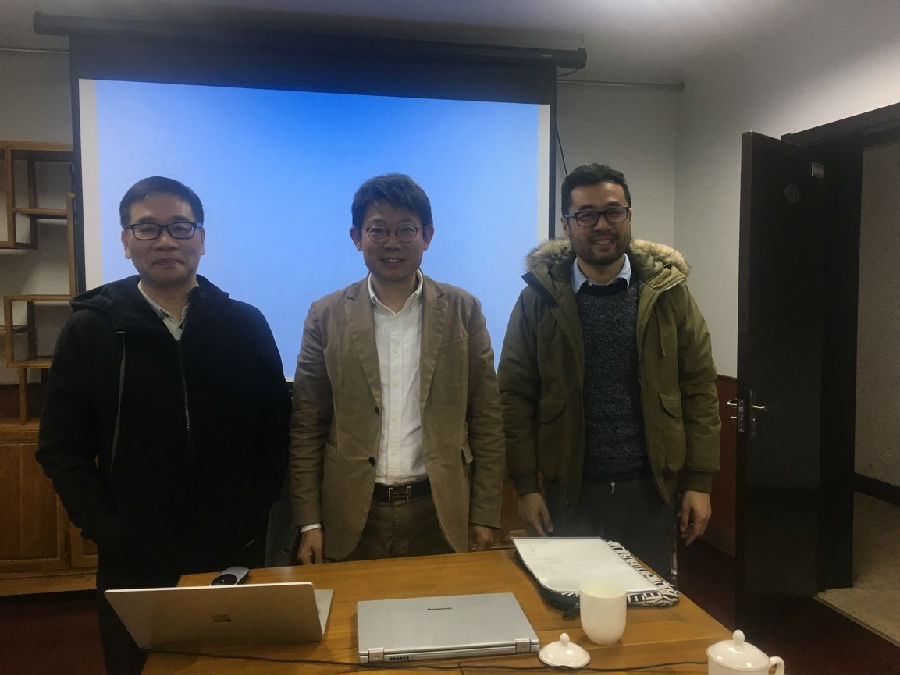
讲座结束后,陈金华对讲座的价值与意义做了总结。陈金华指出,对佛教的国际化、东亚化、原典化的转向,贡献巨大。东亚佛教是否还是纯正的佛教传统?这对东亚的信众是一个具有极强冲击力的拷问。西欧的“局外人”与东洋“信众”之间的沟通与碰撞,为现代研究者提供了反思、选择不同路径的机遇:究竟是“佛教的原意”有意义,还是人们现实中信仰的、发挥作用的佛教有意义?陈金华教授认为,研究佛教在历史上如何发生作用、为何被屡屡重新诠释,才是佛教研究的意义所在。但发源于西方的佛教文献学路径,使佛教趋于科学化,符合学术传统,其价值与意义同样不能被抹杀,Buddology与Buddhist Study两种进路与方法的融合,才是佛教研究的最佳路径。
讲座最后,陈继东就本次讲座的主题,与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机构的师生进行了交流。
3月1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三讲举办,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陈永革研究员作题为“人的发现:民国时期(1912~1949)佛教界对僧众公民性与佛教公共性的思考及其效应”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圣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哲学系邵佳德助理研究员等出席本次讲座。

陈永革以西方近代的两次“人的发现”作为反思与透视晚清民国中国佛教界一系列“变与不变”的切入点,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何思考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对于这一问题,陈永革认为,必须从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与宗教的演变等不同视角进行审视,但“人的现代性”始终是审视这一问题的最关键处。要回答如何思考中国佛教的现代性,首先要定义何为中国佛教的现代性。陈永革研究员认为,这虽是一个目前尚无确论的问题,但其脉络与主流,却有迹可循。不同于时代性,现代性是一个时代成熟的标志,是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回应。现代性的反思,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在时代中的实践之上。中国的佛教现代性有三重结构。
一是“僧人生态”与“佛教处境”,(教化与处境)。此处所谓“生态”,指涉的是佛教所有独特的一种结构,包括面对生命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态度两个方面。生态与处境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互动,生态不仅要适应处境,还在这一过程中重塑着处境。民国时期由高僧所极力提倡的僧政、僧格等观念,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僧人对公民身份、对社会环境的理解及其实践方向。
二是“教化观念”与“文化理念”(教化与文化)。佛教从“教化”到“文化”的转变,是在晚清民国大变局中的一次扩展自身影响力边界的尝试与努力,也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边界的扩展,必然要求对佛教的“生态”进行重新解释,比如在民国时期佛教界广泛存在的僧人等级的划分。但是,这一过程开始的太快,导致佛教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缺少应有的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显著的特征有三:佛教的知识化、佛教艺文化与佛教多元化。
三是“舆论意识”与“理论意识”(舆论与理论)。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从高扬“理性”发展为理论意识的普遍发展,各种理论层出不穷。相比之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不是理论的生产,而是舆论的营造。“舆论意识”的强化是民国佛教有别于以往佛教的重要标识之一,是与这一时期佛教的“生态”与“处境”密切相关的,同时又对“生态”与“处境”产生作用。舆论很重要,但是不能止步于此,佛教向文化、文明的转型,必然要求理论化。如何从“重舆论”转向“重理论”,是中国佛教“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
最后,陈永革从“公共性”的角度,对何以民国佛教特重舆论进行了说明。佛教虽然自有其教义教理系统,但从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来看,始终存在着以吸收、转换思想资源的方式应对以儒家、道教为代表的外界刺激与挑战的传统。民国佛教推崇舆论意识的根本原因,是对佛教公共性的期待,是将佛教从个人修行、修学、解脱转变为公共教育的期待。此外,至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帝制国家到共和制国家的转向,佛教自唐代起所获得的“圣教”地位,在奉行信仰自由、以政教分离确保宗教多元共存格局的社会环境中,开始逐渐下降——虽然“圣教”之“圣”完全是儒家传统的评价标准,但这并不妨碍自唐至民国千余年来信众对佛教崇高地位的认知与认可。在这一时期,由于对佛教理解的不同,佛教所遭遇的挑战与冲击不仅来自其他宗教,还有来自哲学的竞争压力。公共领域内存在的竞争局面,也是促使佛教采取公共话语方式进行回应与自我表达的动因之一。
圣凯从三个方面对陈永革的讲座进行了评价与回应。首先,陈永革指出的“现代化”、“公民性”等观念,还可以从实践、行动的层面展开研究。其次,要把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区分,现代性是有危机的,现代化是一种自觉。要化解现代性的问题,就需要现代化的方法。第三,对于审视民国佛教波澜壮阔的图景,“现代性”的视野确实“简短有力”。
讲座的最后,陈继东就本次讲座的主题,与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院校机构的师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3月2日“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系列讲座”第四讲“经史之间:晚清民国汉传佛教学术史的建构”举办,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龚隽教授主讲,圣凯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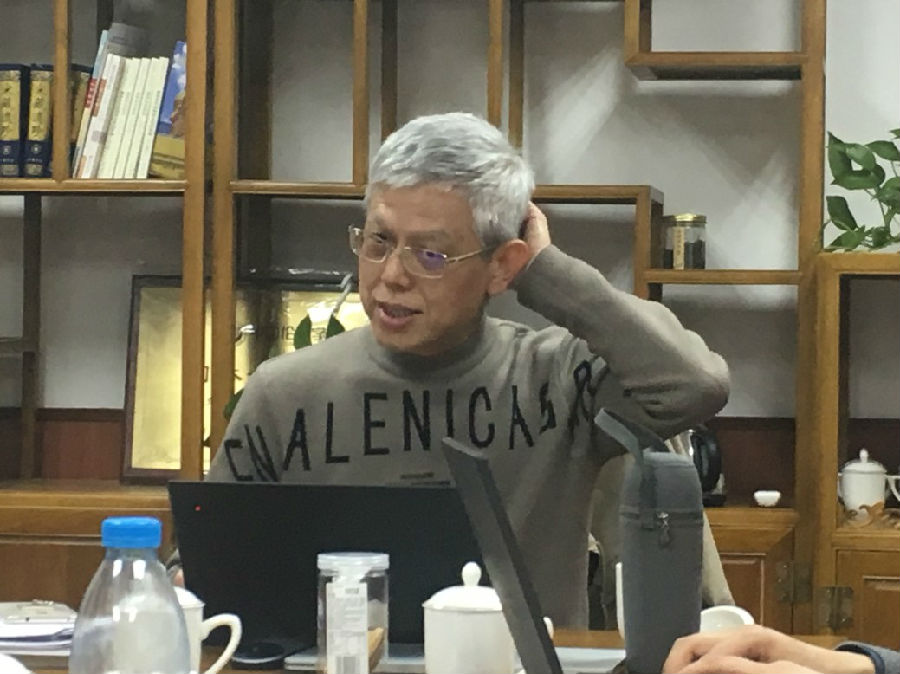
龚隽认为,现在对于佛教史和佛教思想的理解,有意无意间仍然还受着晚清民国以来所建立的佛教学术图式的桎梏,这是需要反思的。从西方学术的视角切入,很多问题普遍都被遮蔽掉了。但是从传统学术的脉络看,特别是在佛教经学和佛教史学的架构里面看,很多“问题”就会显豁出来。我们不能将近代佛教简单理解为新知基础上的重建,实际上晚清到民国中国佛教史的建立是在旧学和新知非常复杂的交叉的观念下的产物。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和佛学的复兴本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特别是晚清佛教学的兴起,其实和今文经学的关系很密切。新史学在佛教学建设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新史学运动中,佛教的经典降格为一般的史料,了解佛教经典和思想的流变也必须通过语言历史的批判来实现。近代佛学研究的重镇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无不是以这种方式进行佛教研究。然而,经学和史学的关系,其实是道体与事相的关系。近代佛教面对西方学术方法的传入,面对历史方法对佛教作为“经学”神圣性的解构,在信仰与知识之前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一点在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的路径选择上、尤其是欧阳竟无的佛教研究中体现的极为明显。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佛教知识史建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理解晚清到民国以来中国佛教知识史建立时不可回避的议题。晚清以来佛学大多是从日本取得近代性知识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为中国学术史和知识史奠定了新的文化基层建构。

讲座结束后,圣凯进行点评,对讲座中提出的信仰与知识化研究取径、经典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等问题深表赞同。圣凯用“佛法是不发展的,佛教是发展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概括。
讲座最后,龚隽与来自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机构的师生就讲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互动。
